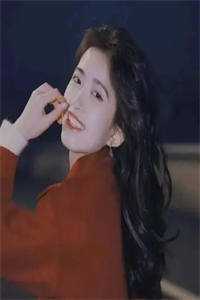点击阅读全文
小说:重振大明
类型:穿越小说
作者:韭菜东南生
角色:朱宇洪承畴朱慈烺
 第九章 黎民为重
“这件事做好了,等你回到京师,本宫会为你请功,如果做不到,本宫就要你的脑袋!”朱慈烺冷冷说。
马绍愉额头上冒出细密的冷汗。
“怎么?不行?”朱慈烺脸色变了。
“臣……遵命。”
马绍愉没有拒绝的权力,只能咬牙答应。
朱慈烺点点头,接着说:“如果你到了杏山,发现杏山被围,千万不可犹豫,要立即带着塔山军民撤退,如果朝廷有责罚,本宫自会替你担待。”
壮士断腕。
前方军情多变,朱慈烺不能保证建虏大军还在锦州。
如果建虏到了杏山,马绍愉到时犹豫不决,耽误了时间,很可能会把塔山也填进去,因此,他要事先提醒。
马绍愉说不出话,脑子里嗡嗡的,从见皇太子第一秒他就蒙,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劲来。
“杏山塔山两地居民,不论是兵是民,只要他们回到关内,朝廷就给他们分田地。
还有,如果宁远、山海关或者其他地方的辽民愿意跟你回来,也一概欢迎。
总之一句话,你带回来的辽民越多,你的功劳就越大,你听明白没有?”
朱慈烺提高声音。
听到这里,马绍愉的脑子终于总算是反应过来了,什么?分田地?
朝廷哪有那么多地分给难民?皇太子这不是信口开河吗?
脸上很自然就表露出了茫然。
朱慈烺皱眉:“我的话你没听见?”
“臣听见了,但……臣不明白,圣旨里没写这些啊。”
马绍愉壮着胆子问。
“圣旨没有写,这是本宫的命令,怎么,你想抗命?”
朱慈烺脸色一沉。
“臣不敢。”
马绍愉吓一哆嗦。
如果是海瑞那样的直臣,朱慈烺敢这么说,他就敢直接翻桌子:
“臣就是抗命,抗乱命!你要怎么地?”
但马绍愉不是海瑞,他没有海瑞的胆。
“地的事你不用担心,本宫既然让你这么说,就一定能做到。
放心,你还不值得本宫骗。”
朱慈烺为马绍愉宽心。
马绍愉心想,是啊,皇太子为什么要骗我?
看我不顺眼直接杀我就行了,何必这么费劲?
一咬牙,心想反正是皇太子说的,有地没地,先把那些难民骗回关内再说。
至于后续,就让他们找皇太子吧,皇太子乃我大明储君,万众瞩目,应该不会赖到我头上。
对了,我要沿途宣扬,让他们都知道皇太子要给他们分地,到时皇太子想赖也赖不掉。
于是大声说:“臣明白了。”
“这一次公干,户部拨了你多少银子?”朱慈烺问。
“一百两。”
兵部职方司郎中,堂堂五品官,去执行这么大的任务,一万多人的撤退,竟然只有区区一百两经费。
又或者在户部看来,只须将难民领回来就是,沿途从宁远、山海关取食,根本不需要太多的银子。
朱慈烺不意外,他向田守信点点头,田守信从衣袖中取出一张银票,交到马绍愉的手里。
马绍愉一看,大吃一惊。
居然是一张两千两的银票!
这两千两是朱慈烺好不容易从母后那里求来的。
“这两千两你先拿着,如果不够,等你回来本宫给你报销,你记着,所有的钱都要花在辽民身上,让他们吃饱、穿暖,不使一人掉队,如果你敢贪墨一钱,本宫就诛你九族!”
“臣不敢!~”马绍愉吓的拜伏在地。
朱慈烺迈步要走,忽然想起了什么,站住脚步,对马绍愉深深一鞠:
“马绍愉,杏山塔山,两万大明子民的性命就交给你了,本宫在京师等着你的好消息,拜托了!”
“啊!”
马绍愉额头上的冷汗,刷的就流了下来,吓的连连叩首:“殿下不可!不可啊!臣该死,臣有罪啊!”
太子一鞠,一声拜托,岂是他能承受的?
惶恐不安,不可名状。
朱慈烺本尊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,朱慈烺此时也是有感而发,一时控制不住,将前世的礼节用在了这里。
“你现在就出发,记着,带回来的辽民越多,你功劳就越大!”
朱慈烺迈步离开。
马绍愉跪伏在地,直到朱慈烺脚步远去,他才猛的直起身来,泪流满面的说:“臣赴汤蹈火,万死不辞!”
……
打发了马绍愉,一路返回宫中,朱慈烺见田守信欲言又止的样子,于是笑问:
“你好奇我什么要马绍愉带那么多辽民回来,是不是?”
“不。”
田守信摇头:“奴婢是担心。”
“担心什么?”
“奴婢担心马绍愉在外面乱说,坏了殿下你的声誉。”
田守信说。
显然,田守信也不觉得朱慈烺能找来田地给辽民们分,
一旦马绍愉大肆宣扬,到最后兑现不了,朱慈烺的声誉必定会受到影响。
朱慈烺笑了:“放心,田地会有的……”
顿了顿:“银子也会有的。”
回到宫中,朱慈烺取出纸笔,写出自己计划中的几个关键,琢磨了一会,将其中可能的漏洞一一补齐,觉得有点累,就躺床上休息,不想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
睡梦里,他又回到了前世,回到了临时前在河边,又看见那个叫刘志的一把将他推下桥……好狠的一个小孩儿。
待到醒时,田守信已在榻前等候。
“什么时辰了?”朱慈烺一跃而起。
“未时初。”
朱慈烺点点头,原来刚睡了一个多时辰。
“殿下,成国公朱纯臣、定国公徐允祯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正在宫门外候着呢。”
田守信说。
崇祯的圣旨是太子代朕巡视京营,因此兵部和京营都不敢怠慢,两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早早就在宫门外候着了。
“朱纯臣、徐允祯!”
朱慈烺心里冷笑一声。
作为第十二代成国公,朱纯臣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嫡传后代,深受崇祯倚重。
崇祯三年进太傅,九年任京营总督,统领京师全部兵马,崇祯给了他莫大的荣宠,然这位国公爷并没有多少忠君之心,非但没有把京营操练好,反而在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,不加抵抗就开城投降,事后又和陈演一起劝李自成称帝,可谓无耻之尤。
定国公徐允祯是徐达的后代,徐达是世之名将,本人受封中山王,长子承袭魏国公,留在南京,数代为南京守备;
幼子封定国公爵,随着文皇帝迁都北京,传到徐允祯这里已经是九代,因为祖上的赫赫声名,所以徐允祯也是京营轮流坐庄的庄家之一。
徐家世受国恩,但十七年北京城破的时候,徐允祯却想也没想的就投降了李自成。
这么两个尸位素餐、不忠不义的“勋贵”,朱慈烺一开始就抱了必杀之心。
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。
至于兵部尚书陈新甲,历史上他最有名的就是得了崇祯默许,秘密跟满清谈和。
不意竟将双方往来的重要信函随手放置在桌上,被书童以为是塘报而抄发了出去,结果满朝震惊。
清流们愤怒无比,我堂堂大明,岂能跟建虏谈和?
纷纷弹劾陈新甲,连带着也指桑骂槐了崇祯。
崇祯一怒之下将陈新甲下狱,最后处死,陈新甲死的不冤,不但做事不密,行事也颇为冲动。
松锦之战如果不是他立主速战,洪承畴也不会败的那么惨。
不过陈新甲还算有点干才,历史上,正是他的上书举荐,孙传庭才以从牢中脱困,任兵部右侍郎,并被崇祯派往陕西练兵。
尤其是松锦战败后,他筹集钱粮,整经备武,颇有知耻而后勇,想要立功赎罪的意思,因此,朱慈烺暂时忍了他了。
“还有,少詹事王铎和左庶子吴伟业在殿门外求见。”
田守信说。
“就说我身体不舒服,让他们回去吧。”
王吴这两位“东宫老师”几乎每天都求见,朱慈烺早已经习惯了。
“是。”
田守信退出去。
两个宫女为朱慈烺整理衣冠。
这时,一个三十多岁,身穿飞鱼服,腰杆英挺的锦衣卫疾步走了进来。
第九章 黎民为重
“这件事做好了,等你回到京师,本宫会为你请功,如果做不到,本宫就要你的脑袋!”朱慈烺冷冷说。
马绍愉额头上冒出细密的冷汗。
“怎么?不行?”朱慈烺脸色变了。
“臣……遵命。”
马绍愉没有拒绝的权力,只能咬牙答应。
朱慈烺点点头,接着说:“如果你到了杏山,发现杏山被围,千万不可犹豫,要立即带着塔山军民撤退,如果朝廷有责罚,本宫自会替你担待。”
壮士断腕。
前方军情多变,朱慈烺不能保证建虏大军还在锦州。
如果建虏到了杏山,马绍愉到时犹豫不决,耽误了时间,很可能会把塔山也填进去,因此,他要事先提醒。
马绍愉说不出话,脑子里嗡嗡的,从见皇太子第一秒他就蒙,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劲来。
“杏山塔山两地居民,不论是兵是民,只要他们回到关内,朝廷就给他们分田地。
还有,如果宁远、山海关或者其他地方的辽民愿意跟你回来,也一概欢迎。
总之一句话,你带回来的辽民越多,你的功劳就越大,你听明白没有?”
朱慈烺提高声音。
听到这里,马绍愉的脑子终于总算是反应过来了,什么?分田地?
朝廷哪有那么多地分给难民?皇太子这不是信口开河吗?
脸上很自然就表露出了茫然。
朱慈烺皱眉:“我的话你没听见?”
“臣听见了,但……臣不明白,圣旨里没写这些啊。”
马绍愉壮着胆子问。
“圣旨没有写,这是本宫的命令,怎么,你想抗命?”
朱慈烺脸色一沉。
“臣不敢。”
马绍愉吓一哆嗦。
如果是海瑞那样的直臣,朱慈烺敢这么说,他就敢直接翻桌子:
“臣就是抗命,抗乱命!你要怎么地?”
但马绍愉不是海瑞,他没有海瑞的胆。
“地的事你不用担心,本宫既然让你这么说,就一定能做到。
放心,你还不值得本宫骗。”
朱慈烺为马绍愉宽心。
马绍愉心想,是啊,皇太子为什么要骗我?
看我不顺眼直接杀我就行了,何必这么费劲?
一咬牙,心想反正是皇太子说的,有地没地,先把那些难民骗回关内再说。
至于后续,就让他们找皇太子吧,皇太子乃我大明储君,万众瞩目,应该不会赖到我头上。
对了,我要沿途宣扬,让他们都知道皇太子要给他们分地,到时皇太子想赖也赖不掉。
于是大声说:“臣明白了。”
“这一次公干,户部拨了你多少银子?”朱慈烺问。
“一百两。”
兵部职方司郎中,堂堂五品官,去执行这么大的任务,一万多人的撤退,竟然只有区区一百两经费。
又或者在户部看来,只须将难民领回来就是,沿途从宁远、山海关取食,根本不需要太多的银子。
朱慈烺不意外,他向田守信点点头,田守信从衣袖中取出一张银票,交到马绍愉的手里。
马绍愉一看,大吃一惊。
居然是一张两千两的银票!
这两千两是朱慈烺好不容易从母后那里求来的。
“这两千两你先拿着,如果不够,等你回来本宫给你报销,你记着,所有的钱都要花在辽民身上,让他们吃饱、穿暖,不使一人掉队,如果你敢贪墨一钱,本宫就诛你九族!”
“臣不敢!~”马绍愉吓的拜伏在地。
朱慈烺迈步要走,忽然想起了什么,站住脚步,对马绍愉深深一鞠:
“马绍愉,杏山塔山,两万大明子民的性命就交给你了,本宫在京师等着你的好消息,拜托了!”
“啊!”
马绍愉额头上的冷汗,刷的就流了下来,吓的连连叩首:“殿下不可!不可啊!臣该死,臣有罪啊!”
太子一鞠,一声拜托,岂是他能承受的?
惶恐不安,不可名状。
朱慈烺本尊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,朱慈烺此时也是有感而发,一时控制不住,将前世的礼节用在了这里。
“你现在就出发,记着,带回来的辽民越多,你功劳就越大!”
朱慈烺迈步离开。
马绍愉跪伏在地,直到朱慈烺脚步远去,他才猛的直起身来,泪流满面的说:“臣赴汤蹈火,万死不辞!”
……
打发了马绍愉,一路返回宫中,朱慈烺见田守信欲言又止的样子,于是笑问:
“你好奇我什么要马绍愉带那么多辽民回来,是不是?”
“不。”
田守信摇头:“奴婢是担心。”
“担心什么?”
“奴婢担心马绍愉在外面乱说,坏了殿下你的声誉。”
田守信说。
显然,田守信也不觉得朱慈烺能找来田地给辽民们分,
一旦马绍愉大肆宣扬,到最后兑现不了,朱慈烺的声誉必定会受到影响。
朱慈烺笑了:“放心,田地会有的……”
顿了顿:“银子也会有的。”
回到宫中,朱慈烺取出纸笔,写出自己计划中的几个关键,琢磨了一会,将其中可能的漏洞一一补齐,觉得有点累,就躺床上休息,不想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
睡梦里,他又回到了前世,回到了临时前在河边,又看见那个叫刘志的一把将他推下桥……好狠的一个小孩儿。
待到醒时,田守信已在榻前等候。
“什么时辰了?”朱慈烺一跃而起。
“未时初。”
朱慈烺点点头,原来刚睡了一个多时辰。
“殿下,成国公朱纯臣、定国公徐允祯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正在宫门外候着呢。”
田守信说。
崇祯的圣旨是太子代朕巡视京营,因此兵部和京营都不敢怠慢,两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早早就在宫门外候着了。
“朱纯臣、徐允祯!”
朱慈烺心里冷笑一声。
作为第十二代成国公,朱纯臣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嫡传后代,深受崇祯倚重。
崇祯三年进太傅,九年任京营总督,统领京师全部兵马,崇祯给了他莫大的荣宠,然这位国公爷并没有多少忠君之心,非但没有把京营操练好,反而在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,不加抵抗就开城投降,事后又和陈演一起劝李自成称帝,可谓无耻之尤。
定国公徐允祯是徐达的后代,徐达是世之名将,本人受封中山王,长子承袭魏国公,留在南京,数代为南京守备;
幼子封定国公爵,随着文皇帝迁都北京,传到徐允祯这里已经是九代,因为祖上的赫赫声名,所以徐允祯也是京营轮流坐庄的庄家之一。
徐家世受国恩,但十七年北京城破的时候,徐允祯却想也没想的就投降了李自成。
这么两个尸位素餐、不忠不义的“勋贵”,朱慈烺一开始就抱了必杀之心。
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。
至于兵部尚书陈新甲,历史上他最有名的就是得了崇祯默许,秘密跟满清谈和。
不意竟将双方往来的重要信函随手放置在桌上,被书童以为是塘报而抄发了出去,结果满朝震惊。
清流们愤怒无比,我堂堂大明,岂能跟建虏谈和?
纷纷弹劾陈新甲,连带着也指桑骂槐了崇祯。
崇祯一怒之下将陈新甲下狱,最后处死,陈新甲死的不冤,不但做事不密,行事也颇为冲动。
松锦之战如果不是他立主速战,洪承畴也不会败的那么惨。
不过陈新甲还算有点干才,历史上,正是他的上书举荐,孙传庭才以从牢中脱困,任兵部右侍郎,并被崇祯派往陕西练兵。
尤其是松锦战败后,他筹集钱粮,整经备武,颇有知耻而后勇,想要立功赎罪的意思,因此,朱慈烺暂时忍了他了。
“还有,少詹事王铎和左庶子吴伟业在殿门外求见。”
田守信说。
“就说我身体不舒服,让他们回去吧。”
王吴这两位“东宫老师”几乎每天都求见,朱慈烺早已经习惯了。
“是。”
田守信退出去。
两个宫女为朱慈烺整理衣冠。
这时,一个三十多岁,身穿飞鱼服,腰杆英挺的锦衣卫疾步走了进来。
第十章 代天巡视
此人叫李若链,戊辰武进士出身,时任锦衣卫南堂指挥同知,
甲申之变中,抽签分守崇文门,没多久军士哗变,大部分的京营兵将都跟着出迎,只有李若链和京营副将董琦奋力死战,最后双双战死在城头--
李若链是甲申之变中唯一一个有记载战死城头的锦衣卫官员。
朱慈烺穿越而来,身边没有多少可以信任的人,急需招揽人马,而殉国的那些忠臣烈子就成了他最佳的选择。
正好原来的东宫侍卫长也就是他的亲舅舅周镜骑马摔折了腿,于是他趁机把李若链调来东宫。
明朝太子除开国太子朱标之外,其他太子都住在皇宫之中,因此日常的护卫都是由拱卫司也就是锦衣卫负责,
朱慈烺调用李若链,顶替同样也是锦衣卫的周镜,完全顺理成章。
当然了,大家还是奇怪,李若链何德何能,竟然能被太子看上?
一旦太子登基,李若链就成了从龙之人,前途不可限量啊。
除了李若链,朱慈烺还用了一个叫高文采的锦衣卫千户。
高文采,锦衣卫街道坊掌刑千户,宛平人,甲申之变中,组织军民激烈抵抗李自成,
后听说崇祯皇帝已经在煤山自-杀后,归家,闭门,与全家十七口人一起上-吊自-杀殉国。
这样的人,朱慈烺当然要用。
李若链和高文采原本都是默默无闻之人,忽然得了太子重用,自然都是感激涕零,
这一个月来,两人暗地里为朱慈烺做了不少事情。
朱慈烺挥退两个宫-女,李若链在他耳边轻语了两句,他点头:“走吧,两位国公该等急了。”
“臣朱纯臣、徐允祯、陈新甲见过殿下。”
宫门外,朱纯臣陈新甲和陈新甲已经等候多时,见太子出现,赶紧上前迎接。
朱慈烺在微微颌首,脸上带着温和地微笑:“两位国公免礼,部堂免礼。”
朱纯臣相貌堂堂,面色白皙又身材匀称,一把大胡须又黑又密,穿着绯色的蟒袍,看起来颇为威严,不过细细查看一下,却能发现他眼神里有藏不住的忐忑。
皇帝怎么忽然想起让太子巡视京营了,难道是对他有所不满,想要拔掉他京营总督的位置?
不过还好,皇帝没有亲来,只是派了太子,太子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,应该不难糊弄。
徐允祯身材瘦高,眼神同样有点不安,这些年,他和朱纯臣在京营干了不少狗屁倒灶的事,不查还好,一查肯定要出事,
加上崇祯对他并不是太喜爱,所以他心里的不安更胜朱纯臣。
陈新甲面膛黝黑,一脸忧色,松锦之败兵部要付最大的责任,弹劾他的奏折雪片一样的飞进内阁。
因为皇帝没有说话,所以内阁暂时还没有处置他,不过诏狱的牢门已经为他敞开,他随时都可能被问罪下狱,
因此,这半个月来他拼命工作拼命表现,只希望能逃过此劫。
但不想,襄城兵败的消息又忽然传来,三边总督汪乔年被李自成虐,杀,等于又给了他当头一击。
所以他坐立难宁,惶恐不安。
其实兵部尚书并不能管到到京营,京师三大营属于天子亲军,粮饷都是内帑所出,其总督和指挥都是由皇帝信任的勋戚担任,更有皇帝新任的监军太监,
兵部虽然有协理之责,但也就是挂一个名,除非是皇帝亲自下旨,否则那些勋贵才不会鸟兵部呢,京营出了问题,自然也问责不到兵部的头上。
因此,陈新甲的人虽然来了,但他的心思却不在京营,他的心思,全在皇太子朱慈烺的身上。
陛下令太子巡视京营,他隐隐已经猜出,这恐怕是整顿京营的先兆。
另外,中午接到了秘密从杏山塔山撤退的密旨时,他非常意外。
这么多年,他对皇帝的脾气颇为了解,以皇帝宁折不弯、寸土必争的性子绝对不可能下达杏山塔山撤退的旨意,今日怎么改了脾气呢?
直到马绍愉派人给他传消息,他才恍然大悟。
这一切都是因为皇太子!
杏山塔山已然不可守,陈新甲心里非常清楚,不过他却不敢向崇祯建言。
而如果这两地失守了,作为兵部尚书的他,肯定是要承担连带责任,现在皇太子说服皇上从杏山塔山撤军撤民,算是解了他的一个危难。
因此,他对皇太子颇为感激,同时也隐隐有一种,皇太子已经长大,开始干预朝事,朝政即将会有大变的预感。
而就皇太子给马绍愉所下的三道命令来看,皇太子绝对是一个杀伐果断,智谋深远之人。
因此,陈新甲拜见朱慈烺之时,毕恭毕敬,眼神里甚至带着微微的惶恐,
当然了,和马绍愉一样,陈新甲心里也有疑惑,那就是,太子殿下要从哪找到田地分给辽民呢?
京师周围虽然有很多荒山,但都无法耕种。
想破脑袋也想不出,索性不想了。
皇太子非一般人,肯定有独特的解决办法。
见礼完毕,朱纯臣徐允祯陈新甲簇拥着皇太子向京营而去。
朱慈烺身后,田守信、李若链领着一百锦衣卫浩浩荡荡。
京营分三大营,神机营是火器部队,驻守于积忠坊;
三千营是骑兵部队,营中多是蒙古人,驻守于白中坊,但两营现在基本是空架子,只能勉强撑起面子。
所以京营中仍属五军营为重,五军营分为中军、左掖军、右掖军、左哨军、右哨军。
中军也就是勇卫营由孙应元和黄得功分别带领,正在湖广跟罗汝才张献忠相持,其他四营的驻地都在城北,其中左右掖在德胜门驻守,左哨在安定门驻守,右哨在教忠坊驻守。
“殿下,我们先去哪一营呢?”
朱纯臣小心翼翼地问。
朱慈烺淡淡说:“哪一营也不去,令五军营、神机营、三千营城外校场集合,本宫要校场点验!”
听到此言,朱纯臣大吃一惊,差点从马上摔下来,原以为太子只是到各营中巡视,走马观花之下,自己也不怕露出太多破绽,但不想太子居然要来一个“大阅兵”。
如此的大场面,可是十几年都不曾见了,不说手下的兵丁,就是他自己也要手忙脚乱。
一旦出了乱子,占役、吃空饷、操练废弛的问题,想掩盖恐怕也是掩盖不住了。
徐允祯脸色也发白。
陈新甲心里咯噔一下:看来太子是要玩真的啊!
“怎么,不行吗?”
朱慈烺脸一沉。
朱纯臣暗暗咽了一口唾沫,表面不动声色:“殿下,京师三营一共十二万人,除了在外的勇卫营、京师九门的守卫之外,各军加起来尚有七万人,
猝然之间集合,难免手忙脚乱,影响军容事小,影响殿下校场点验事大,依臣之见,不若令各营整顿人马,明天上午再校场点验也不迟。”
“国公,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圣旨的?”朱慈烺冷冷问。
“禀殿下,是午时。”
“可曾下发到各营?”
“岂敢怠慢,立刻就下发了。”
“既然如此,又怎么是猝然集合?又怎么会手忙脚乱?”
朱慈烺声音严厉:“连个区区的校场点验都要准备一晚上,这还是我大明三大营吗?我能等,但建虏能等吗?
一旦建虏兵临城下,难道你也要他们等一晚上,第二天再行攻城吗?”
“这……”
朱纯臣冷汗涔涔而下,他身为国公,祖上两代封王,三百年的显赫,原本对太子并没多少的敬畏,只把太子当成一个小-孩-子,
直到此时才明白,自己实在是小看太子了,赶紧翻身下马,跪倒在地:“臣糊涂,臣这就去召集各营。”
。
第十一章 千里之外
“给你两个时辰,两个时辰内,各营主将副将,连同在京的所有士卒,须全数集中于城外校场,少一人,我就治他们的罪,另外,士卒兵籍名册也要带来,本宫要一一点验!”
朱慈烺冷冷说。
朱纯臣冷汗更多--这是要他的命啊,京营明里十二万,暗里连五万都不到,只不过支取粮饷之时,依然按兵籍名册上的人数,也就是十二万人领取,这中间的五万差额,自然都被领军的勋贵和将领们层层贪墨了。
朱纯臣当了六年的京营总督,对京营的情弊心知肚明,不过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,他接任的时候京营的空额就有四万了,
这六年来,他只不过是萧规曹随罢了,过去就这样,现在还这样,自己又能有什么错?!
不过想归这么想,他心里却十分清楚,一旦兵册上的人数跟实际的兵数差的太多,他这个京营总督肯定是要担责任的。
事到临头,没有其他办法,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朱纯臣打马急匆匆离去,徐允祯向拱手朱慈烺行礼,也慌张的跟了上去,朱纯臣是京营总督,他是京营提督勋臣,两人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,一荣俱荣一损俱损。
和朱纯臣相比,徐允祯胆气更差劲,刚才朱慈烺训斥朱纯臣之时,他吓的脸都白了,额头上的冷汗比朱纯臣还要多,这样的人,怎么能统兵?又岂会不投降?
徐达一脉,竟沦落到这种地步,朱慈烺心里微微叹息。
朱纯臣徐允祯一走,就只剩下兵部尚书陈新甲了。
“殿下,兵部虽不直接管辖京营,但京营的兵籍名册兵部却是有的,不如臣去取来,免的宵小之徒在兵册上面作假。”
陈新甲毕恭毕敬的说。
从太子的所言所行中,他隐隐已经意识到了什么,朱纯臣和徐允祯的表现他也都看在眼里,只觉得这两位国公实在是太蠢,都祸到临头了,居然还不知晓。
“不必了,我们一起去校场,我有两个问题想向部堂请教。”
朱慈烺淡望向前方。
“是。”
陈新甲受宠若惊。
三百顺天府兵在前开路,同时维护街道的秩序,朱慈烺在陈新甲田守信李若链和一百锦衣卫的簇拥下,浩浩荡荡去往城外的校场。
“哇,是太子爷!”
沿途的街道上,不时有人惊呼,还有人在街边跪下,连连叩首。
朱慈烺头戴翼善冠,穿大红龙纹便服,外面罩着黑色的狐领披风,玉带黑靴,腰悬长剑,骑在一匹浑白的高大骏马上,面色淡淡,不怒不喜,虽然年纪还不大,但却已经有了天家的威仪。
有明一朝,皇帝和太子很少出现在京师街头,因此,朱慈烺此行迅速轰动了整个京城,街上人潮涌动,人人都想要看一看当朝太子长什么样?
前世里,即使是最红的影视明星,也难有这样的待遇。
朱慈烺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,反而满心的悲伤。
他看到,百姓们脸上个个都有菜色,即使是街边那些开着大商铺的商人,也很少有油光满面的,街道两边每一处的避风中,都有衣衫褴褛的乞丐在蜷缩,或三五,或一二,
“皇太子”的呼喊都震天了,但却依然有一半的乞丐动也不动,就好像他们早已经冻死在了昨晚的寒风中一样。
这都是我朱家的子民啊。
京师都这样了,那干旱连连的陕西山西,岂不到处都是乞丐?
饥民的问题不解决,大明朝终究是无救。
朱慈烺心情越发沉重。
……
千里之外。
南直隶徽州。
不比京师的寒冷,徽州的春天温暖而舒适,七八个衣不蔽体的大小乞丐横七竖八的躺在土地庙前的空地上,晒太阳,捉虱子。
一个人骂:“老狗,你儿子怎么还不回来,该不是跑了吧?”
叫老狗的老乞丐赶紧坐起身来,满脸堆笑:“大王哪里话?小狗就是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跑的,兴许是有什么事耽搁了。”
叫大王的那乞丐一瞪眼:“再等一炷香,还不回来,你他么就给我去找!”
其他乞丐纷纷抗议:“老狗,你儿子太不靠谱了,太阳都朝西了还不回来,他该不是想要饿死我们吧?”
“再等等再等等。”
老狗连连赔礼,心里却也忍不住发恨:小王八蛋死哪去了?
一会,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摇摇晃晃的顺着山道走了上来,
“小狗回来了!”
老狗惊喜的跳起来。
其他乞丐也纷纷跳起,一窝蜂的冲向小狗。
“小狗,吃的呢?”
“咦,你背着什么?”
吃惊愤怒之后,乞丐们忽然发现小狗背着一个包袱,于是不由分说的就把包袱抢了下来。
小狗也不反抗,只是张着嘴呵呵傻笑。
包袱解开,里面两只烧鸡。
“哇!烧鸡!”
乞丐们惊喜的声音震动整个土地庙,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
最先解开包袱的那个男乞丐抓住鸡腿,就要往下拧。
“住手!”
老狗从后面追上来,拄着打狗棍,瞪着眼,声嘶力竭的喊:
“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规矩?!大王还没有用呢,哪轮得到你们?”
说着老狗夺了烧鸡,一瘸一拐的回到土地庙,将两只烧鸡捧到大王面前,一脸谄媚:“大王,您先用。”
“老狗不错!”
大王大喜,对老狗的忠心很欣赏,先拧下一根鸡腿赏给老狗,自己再拧下两根御用。
最后将烧鸡往前面一推,不等他说话,群丐就一拥而上,疯狂的抢夺起来。
老狗得了那根鸡腿,狼吞虎咽,三两下就塞到了肚子里,
一抬头,发现小狗呵呵傻笑的站在旁边,不说话,也没有去抢烧鸡,他一下就急了,赶紧喊:“你傻呀?快去抢……”
转头一看,还抢什么抢啊?
不要说烧鸡,连骨头都不剩了。
两只烧鸡,根本不够七八个乞丐分,群丐恨不得把鸡骨头研碎了,都塞肚子里去。
老狗心有歉意,一瘸一拐的走过去,小声叮嘱:“狗儿,下一次你吃饱了再回来。”
“狗儿明白了。”
小狗傻笑。
“小狗,这烧鸡你从哪里弄来的?”
大王吃饱喝足了,一抹嘴,坐在土地庙的台阶上问。
“有一家办喜事,我钻狗洞进去偷出来的。”
小狗回答。
“哈哈,怪不得叫你小狗,你果然是狗!”群丐哈哈大笑。
小狗跟着傻笑。
老狗有点不满,骂小狗不就是骂他吗?
这帮混蛋,端起碗吃饭,放下碗就骂娘!
回头得告诉狗儿,再有偷烧鸡这样的好事,不能便宜任何人,咱父子两人吃独食。
“咦,呀,我肚子疼……”
一个小乞丐忽然抱着肚子,哎哎疼叫起来。
“我也疼。”
更多的乞丐嚎叫起来。
一开始,老狗是不屑的。
这帮人,吃惯了残羹剩饭野菜树皮,忽然吃了烧鸡,肠胃就受不了了,真是废物!
哪像他,不管是野菜树皮还是山珍海味,他都能扛得住,但忽然,他觉得有点不对,肚子传来剧痛,如刀绞一般,双腿一软,噗通一声就摔倒在地,心想,难道我也顶不住了吗?
左右一扫,发现除了狗儿,其他乞丐已都倒在地上了。
隐隐地,老狗觉得有点不对。
 第九章 黎民为重
“这件事做好了,等你回到京师,本宫会为你请功,如果做不到,本宫就要你的脑袋!”朱慈烺冷冷说。
马绍愉额头上冒出细密的冷汗。
“怎么?不行?”朱慈烺脸色变了。
“臣……遵命。”
马绍愉没有拒绝的权力,只能咬牙答应。
朱慈烺点点头,接着说:“如果你到了杏山,发现杏山被围,千万不可犹豫,要立即带着塔山军民撤退,如果朝廷有责罚,本宫自会替你担待。”
壮士断腕。
前方军情多变,朱慈烺不能保证建虏大军还在锦州。
如果建虏到了杏山,马绍愉到时犹豫不决,耽误了时间,很可能会把塔山也填进去,因此,他要事先提醒。
马绍愉说不出话,脑子里嗡嗡的,从见皇太子第一秒他就蒙,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劲来。
“杏山塔山两地居民,不论是兵是民,只要他们回到关内,朝廷就给他们分田地。
还有,如果宁远、山海关或者其他地方的辽民愿意跟你回来,也一概欢迎。
总之一句话,你带回来的辽民越多,你的功劳就越大,你听明白没有?”
朱慈烺提高声音。
听到这里,马绍愉的脑子终于总算是反应过来了,什么?分田地?
朝廷哪有那么多地分给难民?皇太子这不是信口开河吗?
脸上很自然就表露出了茫然。
朱慈烺皱眉:“我的话你没听见?”
“臣听见了,但……臣不明白,圣旨里没写这些啊。”
马绍愉壮着胆子问。
“圣旨没有写,这是本宫的命令,怎么,你想抗命?”
朱慈烺脸色一沉。
“臣不敢。”
马绍愉吓一哆嗦。
如果是海瑞那样的直臣,朱慈烺敢这么说,他就敢直接翻桌子:
“臣就是抗命,抗乱命!你要怎么地?”
但马绍愉不是海瑞,他没有海瑞的胆。
“地的事你不用担心,本宫既然让你这么说,就一定能做到。
放心,你还不值得本宫骗。”
朱慈烺为马绍愉宽心。
马绍愉心想,是啊,皇太子为什么要骗我?
看我不顺眼直接杀我就行了,何必这么费劲?
一咬牙,心想反正是皇太子说的,有地没地,先把那些难民骗回关内再说。
至于后续,就让他们找皇太子吧,皇太子乃我大明储君,万众瞩目,应该不会赖到我头上。
对了,我要沿途宣扬,让他们都知道皇太子要给他们分地,到时皇太子想赖也赖不掉。
于是大声说:“臣明白了。”
“这一次公干,户部拨了你多少银子?”朱慈烺问。
“一百两。”
兵部职方司郎中,堂堂五品官,去执行这么大的任务,一万多人的撤退,竟然只有区区一百两经费。
又或者在户部看来,只须将难民领回来就是,沿途从宁远、山海关取食,根本不需要太多的银子。
朱慈烺不意外,他向田守信点点头,田守信从衣袖中取出一张银票,交到马绍愉的手里。
马绍愉一看,大吃一惊。
居然是一张两千两的银票!
这两千两是朱慈烺好不容易从母后那里求来的。
“这两千两你先拿着,如果不够,等你回来本宫给你报销,你记着,所有的钱都要花在辽民身上,让他们吃饱、穿暖,不使一人掉队,如果你敢贪墨一钱,本宫就诛你九族!”
“臣不敢!~”马绍愉吓的拜伏在地。
朱慈烺迈步要走,忽然想起了什么,站住脚步,对马绍愉深深一鞠:
“马绍愉,杏山塔山,两万大明子民的性命就交给你了,本宫在京师等着你的好消息,拜托了!”
“啊!”
马绍愉额头上的冷汗,刷的就流了下来,吓的连连叩首:“殿下不可!不可啊!臣该死,臣有罪啊!”
太子一鞠,一声拜托,岂是他能承受的?
惶恐不安,不可名状。
朱慈烺本尊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,朱慈烺此时也是有感而发,一时控制不住,将前世的礼节用在了这里。
“你现在就出发,记着,带回来的辽民越多,你功劳就越大!”
朱慈烺迈步离开。
马绍愉跪伏在地,直到朱慈烺脚步远去,他才猛的直起身来,泪流满面的说:“臣赴汤蹈火,万死不辞!”
……
打发了马绍愉,一路返回宫中,朱慈烺见田守信欲言又止的样子,于是笑问:
“你好奇我什么要马绍愉带那么多辽民回来,是不是?”
“不。”
田守信摇头:“奴婢是担心。”
“担心什么?”
“奴婢担心马绍愉在外面乱说,坏了殿下你的声誉。”
田守信说。
显然,田守信也不觉得朱慈烺能找来田地给辽民们分,
一旦马绍愉大肆宣扬,到最后兑现不了,朱慈烺的声誉必定会受到影响。
朱慈烺笑了:“放心,田地会有的……”
顿了顿:“银子也会有的。”
回到宫中,朱慈烺取出纸笔,写出自己计划中的几个关键,琢磨了一会,将其中可能的漏洞一一补齐,觉得有点累,就躺床上休息,不想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
睡梦里,他又回到了前世,回到了临时前在河边,又看见那个叫刘志的一把将他推下桥……好狠的一个小孩儿。
待到醒时,田守信已在榻前等候。
“什么时辰了?”朱慈烺一跃而起。
“未时初。”
朱慈烺点点头,原来刚睡了一个多时辰。
“殿下,成国公朱纯臣、定国公徐允祯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正在宫门外候着呢。”
田守信说。
崇祯的圣旨是太子代朕巡视京营,因此兵部和京营都不敢怠慢,两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早早就在宫门外候着了。
“朱纯臣、徐允祯!”
朱慈烺心里冷笑一声。
作为第十二代成国公,朱纯臣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嫡传后代,深受崇祯倚重。
崇祯三年进太傅,九年任京营总督,统领京师全部兵马,崇祯给了他莫大的荣宠,然这位国公爷并没有多少忠君之心,非但没有把京营操练好,反而在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,不加抵抗就开城投降,事后又和陈演一起劝李自成称帝,可谓无耻之尤。
定国公徐允祯是徐达的后代,徐达是世之名将,本人受封中山王,长子承袭魏国公,留在南京,数代为南京守备;
幼子封定国公爵,随着文皇帝迁都北京,传到徐允祯这里已经是九代,因为祖上的赫赫声名,所以徐允祯也是京营轮流坐庄的庄家之一。
徐家世受国恩,但十七年北京城破的时候,徐允祯却想也没想的就投降了李自成。
这么两个尸位素餐、不忠不义的“勋贵”,朱慈烺一开始就抱了必杀之心。
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。
至于兵部尚书陈新甲,历史上他最有名的就是得了崇祯默许,秘密跟满清谈和。
不意竟将双方往来的重要信函随手放置在桌上,被书童以为是塘报而抄发了出去,结果满朝震惊。
清流们愤怒无比,我堂堂大明,岂能跟建虏谈和?
纷纷弹劾陈新甲,连带着也指桑骂槐了崇祯。
崇祯一怒之下将陈新甲下狱,最后处死,陈新甲死的不冤,不但做事不密,行事也颇为冲动。
松锦之战如果不是他立主速战,洪承畴也不会败的那么惨。
不过陈新甲还算有点干才,历史上,正是他的上书举荐,孙传庭才以从牢中脱困,任兵部右侍郎,并被崇祯派往陕西练兵。
尤其是松锦战败后,他筹集钱粮,整经备武,颇有知耻而后勇,想要立功赎罪的意思,因此,朱慈烺暂时忍了他了。
“还有,少詹事王铎和左庶子吴伟业在殿门外求见。”
田守信说。
“就说我身体不舒服,让他们回去吧。”
王吴这两位“东宫老师”几乎每天都求见,朱慈烺早已经习惯了。
“是。”
田守信退出去。
两个宫女为朱慈烺整理衣冠。
这时,一个三十多岁,身穿飞鱼服,腰杆英挺的锦衣卫疾步走了进来。
第九章 黎民为重
“这件事做好了,等你回到京师,本宫会为你请功,如果做不到,本宫就要你的脑袋!”朱慈烺冷冷说。
马绍愉额头上冒出细密的冷汗。
“怎么?不行?”朱慈烺脸色变了。
“臣……遵命。”
马绍愉没有拒绝的权力,只能咬牙答应。
朱慈烺点点头,接着说:“如果你到了杏山,发现杏山被围,千万不可犹豫,要立即带着塔山军民撤退,如果朝廷有责罚,本宫自会替你担待。”
壮士断腕。
前方军情多变,朱慈烺不能保证建虏大军还在锦州。
如果建虏到了杏山,马绍愉到时犹豫不决,耽误了时间,很可能会把塔山也填进去,因此,他要事先提醒。
马绍愉说不出话,脑子里嗡嗡的,从见皇太子第一秒他就蒙,到现在都还没有缓过劲来。
“杏山塔山两地居民,不论是兵是民,只要他们回到关内,朝廷就给他们分田地。
还有,如果宁远、山海关或者其他地方的辽民愿意跟你回来,也一概欢迎。
总之一句话,你带回来的辽民越多,你的功劳就越大,你听明白没有?”
朱慈烺提高声音。
听到这里,马绍愉的脑子终于总算是反应过来了,什么?分田地?
朝廷哪有那么多地分给难民?皇太子这不是信口开河吗?
脸上很自然就表露出了茫然。
朱慈烺皱眉:“我的话你没听见?”
“臣听见了,但……臣不明白,圣旨里没写这些啊。”
马绍愉壮着胆子问。
“圣旨没有写,这是本宫的命令,怎么,你想抗命?”
朱慈烺脸色一沉。
“臣不敢。”
马绍愉吓一哆嗦。
如果是海瑞那样的直臣,朱慈烺敢这么说,他就敢直接翻桌子:
“臣就是抗命,抗乱命!你要怎么地?”
但马绍愉不是海瑞,他没有海瑞的胆。
“地的事你不用担心,本宫既然让你这么说,就一定能做到。
放心,你还不值得本宫骗。”
朱慈烺为马绍愉宽心。
马绍愉心想,是啊,皇太子为什么要骗我?
看我不顺眼直接杀我就行了,何必这么费劲?
一咬牙,心想反正是皇太子说的,有地没地,先把那些难民骗回关内再说。
至于后续,就让他们找皇太子吧,皇太子乃我大明储君,万众瞩目,应该不会赖到我头上。
对了,我要沿途宣扬,让他们都知道皇太子要给他们分地,到时皇太子想赖也赖不掉。
于是大声说:“臣明白了。”
“这一次公干,户部拨了你多少银子?”朱慈烺问。
“一百两。”
兵部职方司郎中,堂堂五品官,去执行这么大的任务,一万多人的撤退,竟然只有区区一百两经费。
又或者在户部看来,只须将难民领回来就是,沿途从宁远、山海关取食,根本不需要太多的银子。
朱慈烺不意外,他向田守信点点头,田守信从衣袖中取出一张银票,交到马绍愉的手里。
马绍愉一看,大吃一惊。
居然是一张两千两的银票!
这两千两是朱慈烺好不容易从母后那里求来的。
“这两千两你先拿着,如果不够,等你回来本宫给你报销,你记着,所有的钱都要花在辽民身上,让他们吃饱、穿暖,不使一人掉队,如果你敢贪墨一钱,本宫就诛你九族!”
“臣不敢!~”马绍愉吓的拜伏在地。
朱慈烺迈步要走,忽然想起了什么,站住脚步,对马绍愉深深一鞠:
“马绍愉,杏山塔山,两万大明子民的性命就交给你了,本宫在京师等着你的好消息,拜托了!”
“啊!”
马绍愉额头上的冷汗,刷的就流了下来,吓的连连叩首:“殿下不可!不可啊!臣该死,臣有罪啊!”
太子一鞠,一声拜托,岂是他能承受的?
惶恐不安,不可名状。
朱慈烺本尊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,朱慈烺此时也是有感而发,一时控制不住,将前世的礼节用在了这里。
“你现在就出发,记着,带回来的辽民越多,你功劳就越大!”
朱慈烺迈步离开。
马绍愉跪伏在地,直到朱慈烺脚步远去,他才猛的直起身来,泪流满面的说:“臣赴汤蹈火,万死不辞!”
……
打发了马绍愉,一路返回宫中,朱慈烺见田守信欲言又止的样子,于是笑问:
“你好奇我什么要马绍愉带那么多辽民回来,是不是?”
“不。”
田守信摇头:“奴婢是担心。”
“担心什么?”
“奴婢担心马绍愉在外面乱说,坏了殿下你的声誉。”
田守信说。
显然,田守信也不觉得朱慈烺能找来田地给辽民们分,
一旦马绍愉大肆宣扬,到最后兑现不了,朱慈烺的声誉必定会受到影响。
朱慈烺笑了:“放心,田地会有的……”
顿了顿:“银子也会有的。”
回到宫中,朱慈烺取出纸笔,写出自己计划中的几个关键,琢磨了一会,将其中可能的漏洞一一补齐,觉得有点累,就躺床上休息,不想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
睡梦里,他又回到了前世,回到了临时前在河边,又看见那个叫刘志的一把将他推下桥……好狠的一个小孩儿。
待到醒时,田守信已在榻前等候。
“什么时辰了?”朱慈烺一跃而起。
“未时初。”
朱慈烺点点头,原来刚睡了一个多时辰。
“殿下,成国公朱纯臣、定国公徐允祯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正在宫门外候着呢。”
田守信说。
崇祯的圣旨是太子代朕巡视京营,因此兵部和京营都不敢怠慢,两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早早就在宫门外候着了。
“朱纯臣、徐允祯!”
朱慈烺心里冷笑一声。
作为第十二代成国公,朱纯臣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嫡传后代,深受崇祯倚重。
崇祯三年进太傅,九年任京营总督,统领京师全部兵马,崇祯给了他莫大的荣宠,然这位国公爷并没有多少忠君之心,非但没有把京营操练好,反而在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,不加抵抗就开城投降,事后又和陈演一起劝李自成称帝,可谓无耻之尤。
定国公徐允祯是徐达的后代,徐达是世之名将,本人受封中山王,长子承袭魏国公,留在南京,数代为南京守备;
幼子封定国公爵,随着文皇帝迁都北京,传到徐允祯这里已经是九代,因为祖上的赫赫声名,所以徐允祯也是京营轮流坐庄的庄家之一。
徐家世受国恩,但十七年北京城破的时候,徐允祯却想也没想的就投降了李自成。
这么两个尸位素餐、不忠不义的“勋贵”,朱慈烺一开始就抱了必杀之心。
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。
至于兵部尚书陈新甲,历史上他最有名的就是得了崇祯默许,秘密跟满清谈和。
不意竟将双方往来的重要信函随手放置在桌上,被书童以为是塘报而抄发了出去,结果满朝震惊。
清流们愤怒无比,我堂堂大明,岂能跟建虏谈和?
纷纷弹劾陈新甲,连带着也指桑骂槐了崇祯。
崇祯一怒之下将陈新甲下狱,最后处死,陈新甲死的不冤,不但做事不密,行事也颇为冲动。
松锦之战如果不是他立主速战,洪承畴也不会败的那么惨。
不过陈新甲还算有点干才,历史上,正是他的上书举荐,孙传庭才以从牢中脱困,任兵部右侍郎,并被崇祯派往陕西练兵。
尤其是松锦战败后,他筹集钱粮,整经备武,颇有知耻而后勇,想要立功赎罪的意思,因此,朱慈烺暂时忍了他了。
“还有,少詹事王铎和左庶子吴伟业在殿门外求见。”
田守信说。
“就说我身体不舒服,让他们回去吧。”
王吴这两位“东宫老师”几乎每天都求见,朱慈烺早已经习惯了。
“是。”
田守信退出去。
两个宫女为朱慈烺整理衣冠。
这时,一个三十多岁,身穿飞鱼服,腰杆英挺的锦衣卫疾步走了进来。